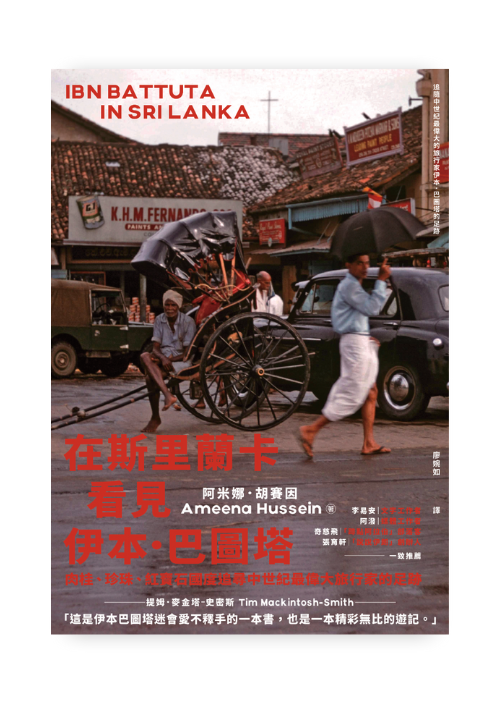生命繼續著,但為什麼?
「未來可能會有一種小說,我們幾乎不知何以名之。」──吳爾芙
繁體中文版獨家收錄親族照片與醞釀經典的吳爾芙日記 名作誕生的時時刻刻
從《出航》、《燈塔行》 吳爾芙「海的書寫」系列最終章
劇場導演 魏瑛娟──導讀
「與其說這是一部小說,不如說這是一場多聲部的內在獨白展演,不僅崩毀了小說形式的刻板想像,也拓開了獨白創作的可能邊界,看似封閉純淨,但又大開大闔波濤壯闊。全書由六個角色的輪流獨白構成,陳述的方式統一穩定,內容卻時空自由事件迻邐,全然不受拘限,彷彿看見六個角色坐在舞台上,交叉吐出詞語「說」出一個世界,戲劇動作是靜態的甚至是單調的,但言說出的世界,湧動立體意象瑰麗,這本小說是可以直接拿來演出的,我邊讀邊想。」──魏瑛娟
吳爾芙出生前,其兄托比因誤診病逝,於是終其一生,吳爾芙都活在其鬼魂的陰影裡。一九二六年,她首度在日記裡試圖「驅魔」,寫下「當我們身不在那裡但依舊存在的事物」這樣一本書的念頭,隨後她將這個想法最早實現於《燈塔行》。而在《海浪》,這個想法推到了最極盡。
六個人物,同時存在也同時缺席於現場──涵蓋一切元素 吳爾芙最終極書寫
吳爾芙賜給了我們靈魂的一生。
──約翰‧雷門(吳爾芙傳記《吳爾芙》作者、吳爾芙夫婦於霍加斯出版社的同事)
《海浪》也許是吳爾芙作品中結構最形式化,敘事本身全然內心化的一部作品。《海浪》透過六個人物不斷的獨白,不斷的獨白,不斷的獨白……呈現九個如散文亦如故事的段落。六個人物用自己描述性的「標籤」或主題曲,在全書中持續地變奏:人物在長大的過程中,漸漸發展出歧異性。隨著死亡和失落陰影的籠罩,漸漸明瞭某些野心和夢想將永遠不會實現,感受到日益年老所帶來的失意悵然。
哥哥托比死後,吳爾芙終其一生活在其幽魂裡。一九二六年,吳爾芙首度在日記裡提及打算寫一本有關「當我們不在那裡而依舊存在的事物」的書,為她自己的靈魂跳一場驅魔舞。一九二九年九月開始動筆的《海浪》,就是這場極致創作的開端……一部沒人看過的小說,一種首度降臨於世的文學類型,她如此堅決,畢竟「怎能允許任何不是詩的文體成為文學」?
太陽尚未升起。
太陽升得更高。
太陽升起。
太陽,升起。
太陽現在升到最高處。
太陽不再站在天空中央。
太陽現在已於天際沉得更低。
太陽在下沉。
現在太陽已經落下。
小說裡有六個人的獨白,也有眾聲齊鳴的九段故事。
有日出、日落,有一天,也有一年。
所有事物的背景都是海浪。
它是吳爾芙決心發明的全新敘事風格──
一種包含了所有元素的飽和文體。
而太陽自海邊的花園升起,在結尾時落下,所有事物背後都是海浪。這些固定出現、純描述的意象插曲,分隔了故事的段落,也是書中唯一的客觀性,其他盡是無休止的內心的獨白。因所有寫實主義的花招盡被丟棄,使其更像是古典戲劇而非小說。
| 內容節錄 |
吳爾芙日記I
春天的第一天
【一九四○年】
十一月三日星期日
昨天河水暴漲過河岸。濕地現在成了一片汪洋,有海鷗在上頭翱翔。L.和我沿路走到飛機棚。河水拍打碎裂,淺綠,湍急,沿著碉堡的破洞傾盆而下。上個月有顆炸彈爆炸;老湯賽先生告訴我那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修補。為了某個原因再度沖破(艾維斯特說河岸因碉堡的緣故而變脆弱了)。今天的雨極大,加上強風。彷彿親愛的大自然在踢掉她的高跟鞋。又回到機棚。洪水愈深愈湍急。橋被沖毀。大水使得農田旁邊的馬路無法通行。所以我所有用來散步的濕地小徑都不見了,還得等到什麼時候呢?河岸又有一處被沖破。它以瀑布的形式溢出:大海不起泡沫。是的,現在洪水緩緩朝著波頓的乾草堆慢慢移動──洪水中的乾草堆──在我們田地中的下方。如果太陽出來會很可愛。今晚的霧有中古世紀感覺。我很快樂可以不用再賺錢;回到P.H.突然文思泉湧的寫作;我很高興的說,這是一塊小畫布。哦,那種自由──
十一月五日星期二
洪水中的乾草堆有著令人無法置信的美……當我抬頭往上看,我看到整塊濕地一片汪洋。在太陽下,呈現深藍,海鷗銜著葛縷子種子;雪風暴;大西洋海岸;黃色島嶼;無葉之樹;紅色小木屋屋頂。哦,我希望洪水永遠持續。處女的唇;沒有平房的蹤跡;彷彿是在萬物的起始。現在前面是鉛灰中帶著紅葉。那是我們內陸的海。凱伯丘現在成了一座懸崖。我心裡想:大學充滿了來自H.A.L.F.中學和崔福楊中學的學生。那是他們的產物。而我:從未如此多產。而我:長期以來對書的渴求仍舊在:真是股幼稚傻氣的熱情。所以如同大家說的,我對於《幕與幕之間》感到非常「高興」而興奮。這個日記的速記會有用。一新風格──去拌合。
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
我應該會喜歡寫下如自然學家──人類自然學家的筆記,我觀察著一本書的節奏如何在我的頭腦中流動著、纏繞成一顆球,一顆令人疲累的球,我將這個觀察視為精神史上一件有趣的瑣事。《幕與幕之間》(最後一章)的節奏如此盤據我的心思,我在自己說出的每個句子裡聽到那個節奏,也許用到那個節奏。我藉著閱讀回憶錄的筆記打破這個節奏。筆記的節奏要求得越加自由、鬆散。我用那節奏寫了兩天,讓我重新提起精神。所以我明天要回去寫《幕與幕之間》。我認為這將會是相當深奧的。
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
在這一刻完成了《露天表演》──還是該取名《波音茲大廳》?──(我大約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開始寫),我正文思泉湧寫著下一本書(尚未命名)的第一章,這將會被命名為《未幾》。今天早上寫的故事我寧願寫露易絲被打斷,她手拿一支玻璃瓶,裡面裝著很稀的牛奶,裡面浮著一小塊奶油。然後我隨著她進廚房,把奶油撇去;我將那塊奶油拿給雷納看。這是戰勝家事的偉大時刻。
我對這本書頗為得意。我想這是採用新方法的一個有趣嘗試。我想這本書比其他的書都要來得能夠呈現精隨。我撇去了更多的牛奶,呈現一塊更豐盛的奶油,當然比悲慘的《歲月》更有新意。我幾乎是樂在其中地寫著每一頁。必須記下一點,這本書只有在寫《羅傑.弗萊的一生》的規律中、在壓力最大休息的時間寫。我會把它當成我的計畫:如果我可以每天規律地寫這本新書──只盼減少這種情況──無論如何,將會有一本關於事實的書來支撐它,然後我將醞釀壓力極高的時刻。我想把爬上山頂──那個持續出現的景象──作為一個起始點。然後看看會出現什麼。如果沒有任何東西,也不打緊。
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日
他們是如此的美,那些老人──我是說父親和母親──多麼單純、多麼清明、波瀾不驚。我沉浸於老舊的信件和父親的回憶錄裡。他愛著她:哦,他是如此坦率、理性、透明──有著如此敏感、纖細的心靈,飽讀詩書而澄澈。甚至是靜謐與爽朗的,他們的生命對我開展:沒有污泥、沒有漩渦。而是如此充滿人性──他們和小孩共處,生命中有著育嬰室的兒歌和哼唱聲。但如果我以現代人的角度來閱讀,我將失去我孩童的眼光,因此我必須停止。沒什麼在騷動;什麼也不投入;不內省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
船帆會有拍動的時候。然後,作為生命藝術的一個偉大業餘者,我決心將我的柳丁吸乾,我像一隻黃蜂,彷彿正在吸食的花朵正在凋萎,如同昨日──我騎馬經過下坡,往上爬升到懸崖。一圈帶刺的鐵絲箍在懸崖邊緣。我沿著紐海芬(Newhaven)路騎,心靈變得生氣勃勃。在那條有住宅的荒涼路上,在溼氣中,年老衣著襤褸的女傭正在買雜貨。騎在馬上看著紐海芬在我眼前劃開。但我身體疲累,心智沉睡。所有想寫日記的欲望都頹廢無力。要如何做才能矯正呢?我必須四處尋找。我想著塞維尼夫人。寫作將成為我每天的快樂。我痛恨老年的僵硬──我已經感覺到它了。我說話的聲音粗嘎。我尖酸刻薄。
腳奔馳向晨露的速度不再如此快速
心對於新情緒的跳動不再如此劇烈
而希望,一旦破碎了,不再如此快速再度迸出
我真的打開馬修.阿諾的詩集,抄下這些詩句。在如此做的同時,我想到為什麼我自己現在不喜歡或是喜歡哪些東西,因為我逐漸遠離階級制度和父權。當代斯蒙讚美〈東科克〉時,我是嫉妒的。我沿著沼地走並自言自語,我是我:我必須跟隨著那張犁:而並非抄襲另一個人。這是我寫作、活著唯一的理由。現在我可以好好享用食物:我以想像創造出來的餐點。
【一九四一年】
元月一日星期三
星期日晚上,我正讀著一本細節精密、有關倫敦大火的書時,倫敦正在燃燒。我的城市有八座教堂被毀,還有工會大樓(Guidehall)。這算是去年的事了。新年的第一天吹著一陣彷彿圓鋸的風。這本書是從三七書店搶救回來的:我從店裡帶回家,連帶幾本伊莉莎白時代的書,好作為我的寫作參考,書名現在叫《嶄新的一頁》(Turning a Page)。心理學家該看得出這些句子,是在那個房間裡,跟某個人,還有一隻狗一起寫出來的。私下附帶幾句:我想在這裡我的贅字或許會少一些──但又何妨,我都寫了那麼多頁了。無須顧慮印刷廠。無須顧慮大眾。
元月九日星期四
一片空白。全覆滿了霜。靜止的霜。燃燒的白。燃燒的藍。榆樹的火紅。我並無意再花筆墨描寫雪裡的低圓山丘;但它自然湧現。就連現在我忍不住要轉頭凝望艾許漢山丘,紅、紫、鴿藍灰,襯托著如此誇張的十字架。那個我總記得──不然就忘了──的句子是怎麼說的。你的最後一眼看什麼都可愛。昨天X太太臉朝下下葬。是個小事故。如此壯碩的女人,像露易絲說的,一時衝動就在墳頭大吃一頓。今天她下葬她的姑媽,那個姑媽的先生在西福(Seaford)目睹了靈異現象。他們的房子遭到炸彈轟炸,是我們上星期某天一大清早聽到的炸彈。L.正在邊發牢騷邊整理房間。這些事情有趣嗎?那種回想:那種說出「停止,你真美?」唉,到我這年紀,生命怎麼都美好。我是說,除了生命本身沒什麼我該追隨的。而山丘的另一邊將無粉紅藍紅的雪。我正在抄寫P.H.。
元月十五日星期三
這本書到最後也許會極為簡潔。同時我對自己的冗長感到羞愧,當我看著那二十本自己寫的書──就堆在我房裡──這樣的感覺便突然襲上心頭。我在為誰感到羞愧?我自己正在翻閱它們。然後聽到喬伊斯的死訊:喬伊斯大概比我小兩個星期。我想起威佛小姐,戴著羊毛手套,拿著《尤里西斯》的打字稿來霍加斯出版社,放在茶几上的情景。我想是羅傑叫她來的。我們該盡心盡力把它印出來嗎?這淫穢的稿子跟當下的場景如此格格不入:她那如老處女般的模樣,釦子扣得緊緊的。而稿子滿是淫穢之詞。我把它放進陳列櫃的抽屜裡。一天凱薩琳.曼斯菲德來了,我把稿子拿出來。她開始讀,取笑它,然後突然說:「但裡面有料:我認為會在文學史上擁有一席地位。」他差不多就在那位置,只是我從沒正視過他。然後我想起湯姆在奧圖林位居葛辛頓的房間裡說到──那時書已經出版了──任何人──在小說最後達到那樣的終極奇蹟以後,他該如何繼續寫下去呢?那時候的他,我第一次見他如此,充滿了狂喜、熱切之情。我買了藍色的平裝本,我想某年夏天我就在這裡閱讀,帶著陣陣驚奇、陣陣新發現,然後再度因為過於乏味而數度中斷。這又回到史前世界。現在所有的男士們正在翻新他們的觀點,而這些⋯⋯
(未完待續)
| 作者簡介 |
維吉尼亞.吳爾芙 Virginia Woolf,生於英國倫敦,雙親皆為各自寡居後再婚,雙方各帶來前夫前妻所生子女。維吉尼亞同父同母的史蒂芬家手足共四人,她排行老三,母親茱莉亞出身出版世家,父親萊斯里‧史蒂芬為文評家。自小以父親為師,家中海量藏書為教材,不曾就學卻因耳濡目染而詩書滿腹。曾與手足一起撰稿、編輯,發行以自宅為名的《海德公園門新聞》。
十三歲時,母親病逝,數年內與維吉尼亞感情親密如母女的姊姊、罹癌的父親接連離世,維吉尼亞精神崩潰。接著是哥哥托比也因誤診而撒手人寰。父親過世後,史蒂芬家四個孩子遷居布倫茲伯利,因托比劍橋的同好每週舉辦例行聚會,形成日後的布倫茲伯利藝文圈。維吉尼亞於二十三歲起在《泰晤士文學增刊》撰稿。
三十歲與雷納德‧吳爾芙結縭。三年後以維吉尼亞‧吳爾芙之名發表《出航》,其重要作品有《戴洛維夫人》、《燈塔行》、《海浪》、《幕與幕之間》、《自己的房間》,以及收錄其大量評論的《普通讀者》與堪稱史詩的《奧蘭朵》。一九一七年,維吉尼亞與雷納德成立了霍加斯出版社,出版了她自己的作品以及布倫茲伯利多位名家的作品。
二次大戰開打前夕,倫敦遭德軍閃電攻擊損傷慘重,維吉尼亞難以承受,精神再度崩潰。在完稿小說《幕與幕之間》之際,她將大衣口袋裝滿石頭,於自家附近投河自盡。
| 譯者簡介 |
黃慧敏,輔仁大學英國文學系、紐約市立大學電影研究碩士。從事教職、字幕翻譯、影評。
海浪 | 吳爾芙經典書寫 一部伴你時時下墜,又刻刻重返平靜的陰翳之書 The Waves
作者 | AUTHOR
維吉尼亞.吳爾芙 Virginia Woolf
出版社 | PUBLISHER
麥田出版
書號 | ISBN
9786263108165
出版日期 | PUBLICATION DATE
2025/03/01
出貨地 | PLACE OF DEPARTURE
台灣